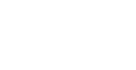孙一圣:不要相信小说家写的非虚构和散文| 创作者访谈
2024-10-21 07:55
2021年至今,小说家孙一圣接受了很多采访。是他的老家、山东菏泽曹县在短视频平台上因一个用乡音喊话的本地人走红,逐渐衍生为文化现象,流行语也很阔气,“北上广曹”。有很多巧合,孙一圣写关于曹县的小说,被归为一种“县城文学”,他家里做曹县当时独两份的丧葬生意,有人在与他的对话中套用了句网络段子,“灵车飘移”。
期间,孙一圣一直处在莫名的、对热度半蹭不蹭的状态,主角是曹县不是自己,这样的曝光好像没有给小说带来很多销量,但多少也扩大了影响力。就在上个月,一位高中同学在购买的杂志上看见了孙一圣,进而找到他的微博,两个人重新联系起来。
除了曹县,孙一圣最为人知的故事是高考过五次,他因而记不起这位第二年重读班上同学的名字。又因为高考战线拉得太长、对高中生活印象太深,他也喜欢不起来自己两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写完这本,我就再也不写高中题材了!”在北京朝阳青年路,他小说经常落款的创作地和家附近,孙一圣正色说。
今年上半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全家福》。为了给主人公、一个留守小孩赵麦生的“出走”故事作脚注,他在书最后附了代跋,讲述自己小时候从曹县到菏泽去找爸妈的真实经历,穿插写到父母把年幼的他和姐姐留在家远走做生意、负债回来后父亲开起了灵车……很多读者说代跋写得好,但他自己却闷闷不乐,似乎将此理解为对小说本身的忽略或批评,懊恼说这篇不选进书里就好了。
写作十多年,全职写作也有七八年,孙一圣经常听到对自己小说的评价是“看不懂”。受意识流代表作家福克纳影响,他的写作思路乃至理想的叙事方式都很复杂,一个人处在曹县小社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可能很寻常,但要写出结构和情节的跌宕,人物关系又会有构思上的变动。他曾为了梳理自己小说与小说之间的联系,往墙上贴一页页的便利贴,再用一根细细的线串起来,形成更清晰的世界观,“泛曹县系统”。
如同他笔下的曹县与网上的没什么关系,他也不喜欢写曹县的小说主角被完全当成自己,“之前很多人看完《还乡》,还以为我结过婚!”《还乡》收录在21年他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夜游神》里,主人公怀胜带新婚妻子回曹县老家,是这个“系统”的开始。主人公也由此更名麦生,曹县故事围绕他一家四口展开,在麦生离家去县城找爸妈的《全家福》后,还会有他交不上学费感到丢脸、离校出走的小说,接下来的小说主角依次是他的母亲、父亲、姐姐……“其实没多少故事,”孙一圣说,“我觉得自己都快掏空了。”
《还乡》的主角叫怀胜,这是孙一圣家谱上的本名。他也的确毕业于《夜游神》里写到的“全县最好的中学”曹县一中,听从过去也是个文青、希望家里有读书人的父亲的指示。母亲没上过学,父亲起码初中毕业,他说。学校图书馆里的余华、余华散文里推荐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和班级订阅的文学刊物成了他的阅读底子。但还是不擅长考试,连达到父亲的要求——考上本科都很艰难,其间还办了一次异地高考,从山东跑到陕西,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他念了一所师范类专科学校,学化学,是报志愿调剂的结果。多次复读的阴影下,大学显得尤其闲散、无聊,他基本上网度过,“我看过唐家三少所有的小说!”这让他从事文学后也未有写网络文学的想法,“每天可能要写五千字,不能断更,一断更就成不了‘大神’了,所以想靠这个挣钱是非常难的。”毕业后他真切体会过挣钱是件难事,继在家乡水泥厂当保安、上海的酒店当服务生之后,顺着父亲说的“普通家庭的人想做成事,得全心投入一件事”,回到大学所在城市郑州的郊区写小说,月租100元。
来到北京、进入文学圈层是2013年。看到北京磨铁文化招图书编辑,孙一圣在自己无相关经验的简历里附了小说,真的得到了面试机会,并入职。当时的文学馆主编是小县城警察出身的作家阿乙,直到今天仍对孙一圣和他的写作青睐有加。当时在磨铁当编辑的文学新人,除了孙一圣,还有已经都有了些名气的邓安庆、里所。后来孙一圣的几份工作也在文艺行业:在一家影视公司,负责收集数据做市场分析,“不喜欢”;在一家新成立的出版品牌当编辑,“讨厌跟人打交道”;还当过独立杂志、电子刊编辑,“还蛮喜欢的,但后来黄了”……
很多文学伙伴在那个阶段认识。孙一圣提到文学论坛黑蓝,当时一个制度是网友轮流当版主,给投稿的小说写评语,有一段时间他的搭档就是《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同时期活跃的还有小说家李唐。和诗人余幼幼、小说家周恺都是文学期刊《天南》当年招募的新人作者,他们的自由投稿都入了选。孙一圣当时上刊的处女作,收录进他尚未开始写曹县、因读多了西方现代派作家而带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你家龙有多少回》,和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在同一个书系。
第一本书的读者反馈不理想,孙一圣在访谈里说过,“一百个好评也抵不住一个差评对作者的伤害”,但“很多时候我也只是想写,跟好坏无关,就是想写。”边上班边写作,从晚上八九点写到凌晨是常态,为了不在冬天暖和的被窝里睡着,他把书桌搬到卫生间,坐在马桶盖上写,又为了集中注意、写快点,他用一块隔板把自己圈在沙发里,写完才能喝水、上厕所。几篇他最满意的小说,都是这样写出来。即使是最早被批评过的那些,他也认为属于刚开始写作的自己元气充沛的时代,“一个年老的作者写不出一部年轻的作品。”
驱动他转为全职写作的是“着急”,工作忙导致作品跟不上,他想赶紧写出第二本书。头几年状态很混乱,要克服惰性、时间充足之后无止境的拖延,“上午写不了还有下午,下午写不了还有晚上,晚上写不了可以也熬到两三点,一天就这么荒废了。”现在他的时间几乎已经模块化,下午三点前是每天坚持的“日课”,两千字左右与曹县无关的故事片段,不讲究体裁,不以发表为目的,也没时间修改。三点后,继续补充曹县“系统”,他的理想是写出二十万字以上的长篇。
以这样的力度,孙一圣过去两年写出了两百万字,这些文字都还没有发表。但创作的流畅、发表相较以前更顺利,没能阻止他陷入某种年龄和时间带来的压力和矛盾。三十五岁后,新的“着急”分成两半,既要让想写的小说落地,从头脑中拿出来,也想要生活的安稳,想结婚。从在郑州写小说租单人间到现在,除了家里的书越来越多,他不怎么讲究环境,也较少出门走动。在北京生活成了习惯,回曹县总是要处理很多家事,难以投入写作状态,父亲对他写小说的期待又是“写个鲁迅那样的”,而不希望他写太多家事,“他要面子”。夹在当中,孙一圣到今天还是没办法特别自洽地把写小说视作一份拿得出手的“职业”。
“我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一个 40 岁就会死掉的人,因为40岁去世的作家特别多,这样我才可以逼自己写下去。”孙一圣说,“至少现在不能停,虽然不能说这是我的创作高峰期,但我要狠狠地抓住我想写的这个阶段,以后写不动了,起码留着这些东西,当日记发也行。”
三明治:《必见辽阔之地》刚出版的时候,你说自己在写一部“不太一样”的小说,写生活里微不足道的事、普通人的想法,就是这本《全家福》吗?
孙一圣:对。这本书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个小孩去找家人要钱、拍合影,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正常的事嘛。我最开始接触文学的时候,发现很多过去的小说好像情节不离奇就不能写成小说似的。我很喜欢福克纳,他有一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讲一个老太太把自己的初恋情人杀了,尸体放在床上留了一辈子,最后老太太死了,镇子里的人才发现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厉害的小说,和很多经典一样是在写一桩隐秘的凶杀案,让我们读起来觉得非常传奇。我之前很受这样的故事影响,在《你家有龙多少回》里就写了好多侦探故事。后面我有点转变了,觉得写普通的、日常的事件也很好,只要写得有起伏,有节奏感。
三明治: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写长?一般来说写短篇会更容易。你对长篇的执念来自哪里?
孙一圣:《全家福》只有九万字,是不知不觉就写长了。我其实一直想写十五字、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可能我阅读的书比较少吧,以前读过的一些经典对我影响还是很大,我不自觉地就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写《全家福》之前,我想到《老人与海》,以前读特别不喜欢,觉得海明威的小说太简单了,和福克纳的差距太大了。后来我发现虽然他只是讲了一个人在海上打渔的故事,没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什么结构变化,但同时,在这个故事里他任何写小说的技巧都没法用,人物也没法拓展,主人公在海上又碰不见什么人。所以最简单的故事反而是最难写的小说,我也在练习。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写短篇的欲望,而是写短篇花费的精力和写长篇是一样的,我觉得划不来。
三明治:番外和代跋是怎么安排的?番外的几个故事,讲“我”跟爸妈一起骑自行车、赶鸭子,都很有意思,为什么它们会成为番外?
孙一圣:番外是我在写《全家福》过程中写的另一些短篇,严格来说不是小说,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一个个片段,类似于一个上午、一天内发生的事。这种体裁我写了好多,这两年每天写一篇,每篇2000字左右,算是给自己安排的写作练习,也可以说是留给长篇小说的素材。选出来的这四篇恰好和《全家福》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赵麦生,都是在讲他、他姐姐、他爸爸、他妈妈这一家四口的事。
代跋,好多人说写得比小说好,觉得我应该这样写小说,有情节,把事情交代清楚。但以《全家福》为例,我的最初想法就是想让读者读这小说到一半还不知道这个小孩为什么跑来跑去的,但为了让作者能看懂一点,做了妥协,不会说孙一圣写的小说根本看不懂。
我以前喜欢的很多小说,比如《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写主人公看见别人在打球,这个人打了一下,那个人打了一下,球进洞了,我读到这里还根本知不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球。再往后读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主人公是个白痴,一开始我只觉得他说话有点笨笨的,但不确定我这个感觉对不对,就带着疑问一直看。然后主人公又描述一个场景,他看见墙上有篱笆的影子,一会变短了,一会又变长了,我才明白他是在说时间,变短是正午到了,变长是下午到了。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我读了这本书,被这种最初的阅读感受给影响到了,这也变成了我的写作偏好。
而且严格说来,代跋里写的也不是全是真事,哈哈,有虚构成分。不要相信小说家写的非虚构和散文。我自己也不很想多写这种,因为太好写了,行文很流畅,这篇代跋就是我一晚上写出来的,当时写了一万多字,已经删了好多。
三明治:你前面说的写故事时一定要拐一个弯儿,不能让读者看得太明白,好像你写作的重点不是在这个故事本身,而是给它安排一个新的叙事方式?类似于解一道题,你就想用另一个公式。
孙一圣:对,是有点这种感觉。反正我不能写好看的故事。我不是没写过,但一写就难受。这个“好看”就是指把事情讲得清晰、明白,读起来流畅。有时候我写着写着会发现自己写得太流畅了,就不往那个方向写了。我觉得作者不能事先把要写什么给挑明,而是让读者自己去读,读进去之后自己思考一阵儿。可能我想得比较多,在情节的编排上有一些小心思,虽然故事很简单,没什么冲突性,但总会让它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出现。这也能让我避免写出流水账来。
三明治:从2018 年到现在,你也全职写作很久了,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职业化倾向的?中间有没有遇到自由职业常见的什么问题,怎么样改善?
孙一圣:职业化倾向是 2021 年左右才开始有的,也就是《夜游神》这本书出版一年后。有句话说的好,一旦不工作,反而也写不了,就是人性、天然的惰性,我不是那种自控力特别强的人。所以要想不工作,集中精力专职写作,你的自控力必须非常之强。比如说我写东西,写着写着就要看一下手机,还要上一下网,翻翻这个书、看看那个书,然后再去喝一杯水。就因为这一天空闲时间太多了!我早晨起来觉得上午写不了,没事还有下午呢,下午也没写,觉得还有晚上,晚上写不了我可以熬到两三点,最后真的熬到两三点了,还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这一天就这么荒废了。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是这么过去的。
这几年我可能是年龄大了,精神上有一种变化,觉得再不写我就该死了。我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明天要死了的作家,本来40岁左右去世的作家也特别多,这样反而能逼自己写。我要是不这么想,还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去写。而且我现在也有规划了,我想写的小说太多了,这辈子都写不完。
孙一圣: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创作期,不能说是高峰期,但是你要狠狠地抓住你想写的这个阶段。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作家,人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写,但他没有抓住、没有去写,我明确地知道现在这个阶段是我最想写点东西出来的。
大概前年开始,我抓住了一个写作的题材,这个东西很微妙,有些很牛的作家一辈子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像福克纳,我觉得他写了那么多小说,都不是好题材,如果换成另一个作家来写,有可能会写成很平庸的小说,但是福克纳用自己非常强大的写作能力把它们写成了经典,而海明威是找到了好的题材。我觉得海明威的写作能力要在福克纳之下,但他的《老人与海》就要比福克纳任何的小说都流传广。
这个题材和曹县没有关系,和我的成长没关系,我觉得是一种意识性的、心灵上向内探索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想把这个小说命名成《心灵简史》,虽然这个名字不好,但题材一定很新,至少是我以前没碰到过的,我以前不会这么写。
三明治:你的小说里也基本是过去的事物,没什么新兴的、当下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你之前还说写不了手机,是不希望它在自己的小说中存在,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
孙一圣:对,我没有写当下的东西。《全家福》写的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事情。我写上世纪 90 年代的东西可以说毫无阻碍,但是要写当下的东西,会有很大的困惑和顾虑。比如我不知道怎么写共享单车,而且问题不在自行车上,而是APP上。任何软件性的东西,我都不想写进小说,但软件又是我们当下很多生活场景中要用的。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比如我写《夜游神》的时候,要写“发微信”,那我可以写成“发消息”,通过词语的变化来模糊掉这个概念,不提这个软件,但是要怎么写“用APP”,对我来说就有点难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纠结的点是这个新兴事物的存在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过段时间会不会就没了?如果是短暂的,我就觉得它在我的小说中不能存在。或者比如说以前的BB机,我觉得我是可以写的,因为它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但手机软件没有实体,我最大的担心是如果我在小说里面写到了它们,但它们过段时间就没了,该怎么办?
孙一圣:我是绝对不会去写 AI 的。但也不一定,如果我解决了这个困惑,可能也会写,只是现阶段我解决不了这个困惑。
孙一圣:睡觉。我现在不喝咖啡、不喝茶,就是为了养觉。白天写困了就睡。有时候看看电影,但是一个人看电影好无聊。旅游总觉得太费时间了。我不怎么出门,有时候会在小区里面走一走,或者比如周恺来北京了,跟他逛一逛颐和园,阿乙有个明确的地点叫我去玩,我就去一下。哈哈,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太惨了,过得好无聊?
三明治:不会,你是很投入在写作上。但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写现实主义题材是否需要作者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去接触更多真实的生活?
孙一圣:我好多朋友也这么说,你整天憋在家里,都没有生活,那你写的啥?我倒是觉得写小说不一定要写真实的生活,生活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印象。写作中真诚最重要,即使这个真诚会伤害到许多人,比如说我写曹县让家人或者一些读者看了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作家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有一些东西如果写深了,可能已经不算是自己的看法了,它有可能是人类共通的意识,是人类对自然、对客观事物的普遍看法。我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只要写我就行了,我自己就是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也不需要过一种复杂的生活,简单的生活也是生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